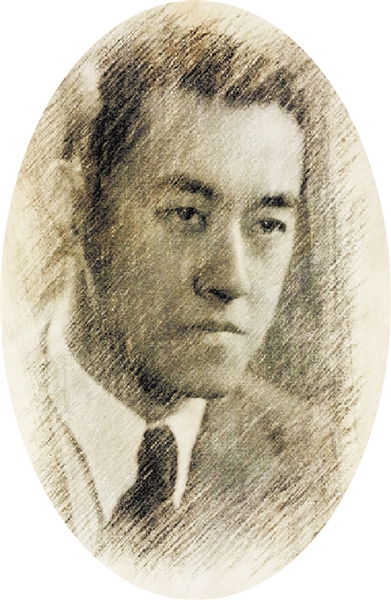
╛lΠό╡Οίφοίχ╢ώβΙί▓▒ίφ?/span>
ί╜ΥόΙΣϊ╗υίδηβί╛ό░Σίδ╜όΩ╢όεθύγΕίφοόηΩί╛Αϊ║ΜΎ╝ΝόΑ╓M╕ΞύΦ▒ί╛Ωϊ╕║ίνπί╕Ιϊ╗υύγΕώμΟϋΝΔόΚΑίΑΣ╓ΑΤήΑΓόεΚϊ╕Α┐UΞίφοϊ║║ώμΟώςρίΞ┤ί╛Ιί░Σί╝ΧϋΥvό│ρόΕΠήΑΓϋ┐βηχ▒όαψίQΝί╜ΥόΩ╢ύγΕίΡΞόΧβόΟΙίψ╣ϊ╕φόΨΘόΟΙϋψ╛αqΣϊ╣Οίδ║όΚπύγΕίζγόΝΒήΑ?/span>
ό╕ΖίΞΟόαψό░Σίδ╜όΩ╢όεθόεΑέΑεό┤ΜΜzϊΠΑζύγΕίνπίφοϊ╣Μϊ╕ΑήΑΓίεραqβόΚΑώμΟόβψ┐UΑϊ╕╜ύγΕΜzΜίφοίιΓώΘΝίQΝίΞ┤όιΨόΒψύζΑίνγϊ╜Ξϊ╕φόΨΘόΟΙϋψ╛ύγΕίΖΙϋκΝϋΑΖήΑΓύ╗ΠΜ╣ΟίφοίχΚββΙί▓▒ίφβίΖΙύΦθόαψόεΑίΖ╖ϊ╗μϋκρόΑπύγΕϊ╕Αϊ╕ςήΑΓώβΙί▓▒ίφβϊ╕ΟίΣρίθ╥Ο(guρσ)║ΡήΑΒώΘΣί▓│ώεΨ≥q╢ύπ░ό╕ΖίΞΟέΑεϊ╕ΚίΚΣίχλέΑζήΑΓϊ╗ΨίΘ°βΊnίνΨϊ║νϊ╕Ψίχ╢ίQΝίνΨ╝εΨύΙ╢ίΤΝϋΙΖύΙΚβΔ╜ίΒγϋ┐Θώσ╒dνΨϊ╜┐ϋΛΓήΑΓώβΙί▓▒ίφβϊ╕φίφοηχ▐pψ╗ύγΕύοΠί╖ηώ╣νώ╛ΕϋΜ▒ίΞΟίφοόικϊ╣θόαψϊ╕ΑόΚΑϋ╡τϋ╡τόεΚίΡΞύγΕόΧβϊ╝γίφοόικήΑΓϊ╗Ψϊ║?918≥q┤ϋΑΔίΖξό╕ΖίΞΟίQΝϊ╕ν≥q┤ίΡΟϋ╡┤ύ╛Οό▒ΓίφοήΑ?926≥q▀_╝Νϊ╗Ψϊ╗ξήΑΛώσυϋΡρϋψ╕ίκηί╖ηίε░όΨ╣όΦ┐ί║εί╝ΑόΦψίΤΝϊ║║ίΠμίψΗί║ούγΕίΖ│╛pΖRΑΜύγΕϋχ║όΨΘίερίΥΙϊ╜?jρσng)ίνπίφοϋΟ╖ί╛ΩίΞγίμτίφοϊ╜ΞήΑΓϊ╕ΞύΦρϋψ┤ίQΝώβΙί▓▒ίφβύγΕό┤ΜόΨΘό░┤≥qδ_Ξ│ϊ╛┐όαψϊ╗ΛίνσύγΕϋχ╕ίνγόΧβόΟΙϊ╣θώγ╛όεδβί╣ϋΔΝύγΕήΑ?/span>
1927≥q▀_╝Νί║ΦόψΞόικϊ╣ΜίΠυίΦνίQΝώβΙί▓▒ίφβίΙ░ό╕ΖίΞΟύ╗ΠΜ╣Ού│╗ϊ╗└LΧβήΑΓίερϊ╕ΛόΥvίΑβϋΙ╣ίΝΩϊ╕ΛόΩ╙η╝ΝώΒΘϋπΒϊ║ΗίΘιϊ╜Ξόφμίερό╕ΖίΞΟϊ╕ΛίφούγΕόικίΠΜίQΝϋψ┤ίΙ░ό╕ΖίΞΟϋΑΒί╕Ιϋχ▓ϋψ╛όΩ╢ϊ╕φϋΜ▒όΨΘ≥q╢ύΦρίQΝί░νίΖ╢ϋχ▓ίΙ░ίΖ│ώΦχύγΕίφοόεψόοΓί┐╡όΩ╙η╝Νϊ╕ΑίχγϋοΒίΑθίΛσίνΨόΨΘόΚΞϋΔ╜ϋπμώΘΛό╕ΖόξγήΑΓίΠςόεΚύν╛ϊ╝γίφο╛p╚ζγΕώβΙϋ╛╛όΧβόΟΙίQΝίΠψϊ╗ξίΒγίΙ░ίΖρϊ╕φόΨΘόΟΙϋψ╛ήΑΓόφμόΚΑϋ░ΥϋρΑϋΑΖόΩιόΕΠΎ╝ΝίΡυϋΑΖόεΚί┐ΔήΑΓϋ┐βϊ╕ςϊ╕Ξ╛lΠόΕΠί╛ΩύθξύγΕί░Πϊ║ΜΎ╝ΝϋποίΛρϊ║ΗώβΙί▓▒ίφβί┐Δϊ╕φ┐UψίΟΜύγΕί╛Αϊ║ΜήΑΓϊ╗ΨόΔΝβΥvίQΝί╜Υ≥q┤ίερϊ╕ΛόΥvώ╗ΕίθΦίΖυίδφύεΜίΙ░έΑείΞΟϊ║▐Z╕ΟύΜΩϊ╕Ξϋχ╕ίΖξίΗΖέΑζύγΕύΚΝίφΡίQΝϊ╫oϊ╗Ψύ╛ηόΕπϊ╕Ξί╖Ν╙ΑΒύΔφϋκΑό▓╕ϋΖ╛ήΑΓϊ╗ΨίΠΙόΔ│ϋ╡°P╝Νϊ╗Οό│Χίδ╜ίζΡϋΙ╣ίδηίδ╜ώΑΦϊ╕φίQΝϋΙ╣ίερίΞ░ί║οήΑΒώΦκίΖ░ήΑΒώσυόζξϋξ┐ϊ║γήΑΒόΨ░ίΛιίζκ╜{ΚίνΕίΒεό│ΛίQΝϊ╗Ψϊ╕Λί▓╕ό╕╕ϋπΙίΠΓϋπΓί╜Υίε░ίφοόικίQΝίΠΣύΟ░ί╜Υίε░ϋΑΒί╕ΙώΔ╜ύΦρίν╥Ο(guρσ)ζΓϋΜ▐pψφύγΕί╜Υίε░ϋψφφaΑόΟΙϋψ╛ίQΝίΡυόζξίΞΒίΙΗίΙ║ϋΑ╗I╝Νϋχνϊ╪ΥέΑεϋ┐βίΠψϋΔ╜όαψϊ╕Αϊ╕ςόχΨό░Σίε░ί┐ΔόΑΒύγΕϋκρύΟ░έΑζήΑΓϋ┐βϊ║δώΔ╜ϊ┐ΔϊΜ╔ώβΙί▓▒ίφβίΗ│ίχγϊ╗ξώβΙϋ╛╛ϊ╕║όοεόι°P╝ΝύΦρϊ╕φόΨΘόΟΙϋψ╛ήΑΓϊ║ΟόαψΎ╝ΝίερίνΘϋψ╛όΩ╢ίQΝϊ╗ΨϋΛ╫Δ║Ηί╛ΙίνπίΛθίντίQΝόΛΛϋχ▓ϋψ╛ϊ╕φό╢ΚίΠΛύγΕίφοόεψόεψϋψφήΑΒόοΓί┐ΈΛφΚϋψΣόΙΡϊ║Ηϊ╕φόΨΘήΑΓί░▒αqβόι╖ίQΝϊ╗Οϊ╗Ψίερό╕ΖίΞΟύγΕύυυϊ╕ΑίιΓϋψ╛ϋ╡°P╝Νηχ▐q║ψϊ╗ξϊ╕φόΨΘϋχ▓όΟΙΎ╝ΝίΠςίερί┐ΖϋοΒόΩ╢όΚΞίερώ╗Σόζ┐ίΗβϊ╕ΛίΟθόΨΘϊ╜εϊ╕║ό│ρώΘΛήΑΓύχΩϊ╕Λϋξ┐ίΞΩϋΒΦίνπόΩ╢όεθΎ╝ΝώβΙί▓▒ίφβίερό╕ΖίΞΟίΖΙίΡΟόΚπόΧβίΘιίΞΒ≥q▀_╝ΝίΠςϊ╪ΥύΧβύ╛ΟώλΕίνΘίΙ╢ύγΕϊ╕ΑύΠφίφούΦθύι┤αqΘϊ╕ΑΜ╞κϊ╛ΜίQΝϋΑΝϋ┐βϊ╣θίΠςόαψίΘ║ϊ║Οί╕χίΛσϊ╗Ψϊ╗υόδ┤όΨ╣ϊ╛┐ίεΌC╕ΟίΞδ_░Ηϋ╡┤ύ╛Οίφοϊ╣ιόΟξϋ╜ρϋΑΔϋβΣόΚΞϋκΝύγΕϊ╛┐ίχεϊ╣ΜϋχκήΑ?/span>
όΩιϋχ║όαψώβΙί▓▒ίφβύιΦύσ╢ύγΕύ╗ΠΜ╣ΟίφοήΑΒϋΔοόΦ┐ίφοίQΝϋ┐αόαψώβΙϋ╛╛όΥΖώΧ┐ύγΕϊ║║ίΠμίφοήΑΒύν╛ϊ╝γίφοίQΝώΔ╜όαψέΑεϋΙ╢όζξίΥΒέΑζήΑΓόφμίδιϊ╪ΥίοΓόφνίQΝόΙΣϊ╗υόδ┤όεΚύΡΗύΦ▐pχνϊ╕║Ύ╝Νϊ╕νϊ╜ΞώβΙόΧβόΟΙϊ╣ΜόΚΑϊ╗ξέΑεϋΙΞαqΣό▒ΓαqεέΑζΎ╝Νόαψίδιϊ╕║ίψ╣╝εΨίδ╜ύΙ▒ί╛Ωό╖▒ό▓ΚίQΝί┐Δϊ╕φώξ▒ίΡτύζΑϊ╕▐Z╕φίδ╜ϊ║Κϊ╕Αϊ╕ςίφοόεψύΜυύτΜίε░ϊ╜ΞύγΕόΔΖόΑΑήΑΓύΦρϊ╕φόΨΘ╛_Σ╓ΘΗίε░ϋκρϋ╛╛ϋξ┐όΨ╥Ο(guρσ)ΑζόΔ│αqβϊ╕Αϊ╣ιόΔψίQΝώβΙί▓▒ίφβϊ┐ζόΝΒϊ║Ηϊ╕Αϋ╛ΙίφΡήΑ?/span>
ύΦρϊ╕φίδ╜ϊζhϋΘςί╖▒ύγΕϋψφφaΑϊ╕▐Z╕φίδ╜ίφούΦθόΟΙϋψ╛Ύ╝Νϊ╕ΞύΜυόΨΘύπΣίοΓόφνίQΝύΡΗί╖ξύπΣόΧβόΟΙϊ║ούΕ╢ήΑΓϊ╕Λϊ╕Ψύ║ς50≥q┤ϊ╗μόΜΖϊΥQαqΘό╕ΖίΞΟίνπίφοίΚψόικώΧ┐ύγΕίΙαϊ╗βό┤▓ηχ▒όαψίΖ╢ϊ╕φϊ╕Αϊ╕ςήΑΓίΙαϊ╗βό┤▓όΩσί╣┤όΛΧϋΊnώζσίΣ╜ίQΝίΠΓίΛιίΡΝύδθϊ╝γίQΝίΡΟόζξϋ╛Ωϋ╜υίνγόικό▒ΓίφοΎ╝Ν╛lΙόΙΡόε║όλ░ί╖ξύρΜίφοίχ╢ήΑ?4ί▓ΒόΩ╢ίQΝϊ╗ΨίΘ▐ZΥQίΝΩό┤ΜίνπίφοόικώΧ┐ίQΝίΑκίψ╝ϊ╕φόΨΘϋχ▓ϋψ╛ίQΝϋΑΝϊ╕Φϋχνϊ╪ΥώταύφΚόΧβϋΓ▓ί┐Ζώκ╗ώΘΘύΦρόευίδ╜όΧβόζΡίQΝϊ╗ΨϋΘςί╖▒ϊ╣θϋΊnϊ╜ΥίΛδϋκΝΎ╝Νί╝Αϊ╗Αϊ╣Ιϋψ╛ηχ▐q╝Ψϊ╗Αϊ╣ΙόΧβόζΡήΑ?932≥q┤ϊΥQόΧβό╕ΖίΞΟόΩ╢ίQΝίΙαϊ╗βό┤▓όΚΑίερύγΕόε║όλ░╛p╒dνγώΘΘύΦρϋΜ▒όΨΘόΧβόζΡόΙΨίΠΓϋΑΔϊ╣οίQΝϋΑΒί╕Ιϋχ▓ϋψ╛ίΤΝίφούΦθϋχ░╜WΦϋχ░ήΑΒϊ║νϊ╜εϊ╕γϊ╣θί╕╕ϊ╕φϋξ┐ίΡΙύΤπήΑΓϊ╜ΗίΙαϊ╗βΜz▓ύγΕέΑεόε║όλ░ίΟθύΡΗέΑζϊ╕Αύδ┤ίΖρϊ╕φόΨΘόΟΙϋψ╛ήΑΓϊ╕ΟίΙαϊ╗βΜz▓ί╖χϊ╕ΞίνγίΡΝόΩ╢ίQΝόεΚϊ╕Αϊ╜Ξϊ╕╗όΝΒϋ┐Θό╕ΖίΞΟί╖ξίφοώβλύγΕώβ╢ϋΣΗόξϊhΧβόΟΙΎ╝Νϋψ╓M╣οόΩ╢ϋΜ▒όΨΘό░┤≥qδ_░▒ί┤φώε▓ίν┤ϋπΤίQΝύΧβ╛θΟί╜ΤόζξόΜΖϊ╗└LψΞόικίεθόερί╖ξ╜EΜύ│╗όΧβόΟΙήΑΓώβ╢ϋΣΗόξ╖ϊ╣θϊ╕Αύδ┤ίζγόΝΒύΦρϊ╕φόΨΘϋχ▓ϋψ╛ίΤΝύ╝ΨίΗβόΧβόζΡΎ╝Νϊ╗Ψϊ║Ο1935≥q┤ύ╝ΨίΗβύγΕήΑΛύ╗βό░┤ί╖ξ╜EΜήΑΜϊ╣θόΙΡϊ╪Υϊ╕φίδ╜αqβϊ╕ΑώλΗίθθόεΑόΩσύγΕόΧβύπΣϊ╣οήΑ?/span>
ίοΓόηεϊ╗ξϊ╕Αϊ╕ςϋψΞόζξόοΓόΜυϋ┐βϊ╕ΑύΟ░ϋ▒κίQΝόΙΣόΔ│ύΦρέΑείφοόεψύΙ▒ίδ╜ϊ╕╗ϊ╣ΚέΑζήΑΓϊ╕Αϊ╕ςίφοϋΑΖίψ╣╝εΨίδ╜ύγΕύΙ▒ίQΝύ╗ζϊ╕Ξόαψίερί░ΛώΘΞϊ╝ι╛lθύγΕίΡΞϊ╣Κϊ╕Μίδ║όφξϋΘςηχΒΎ╝ΝόΛΛίΟΗίΠ▓ύγΕόΧΖύ║╕ίιΗί╜Υϊ╜εώα╗ώγΦόΩ╢ϊ╗μό╜χΜ╣ΒύγΕόΝκύχφύΚΝΎ╝Νϊ╗ξόΚΑϋ░ΥέΑεόευίεθόΑπέΑζόΜΤ╛lζίΡ╕╛U╧xΨ░ύθξήΑΒόΨ░ώβΙϊ╗μϋ░λΎ╝Νϊ╣θϊ╕Ξόαψίξ╜ϊ╕║ίνπφaΑήΑΒϋ┐ΟίΡΙϊ╕ΛόΕΠΎ╝ΝίΠΣϋκρϊ╕Αϊ║δύεΜϊ╝ώg╣Κόφμϋ╛ηϊ╕ξύγΕϋβγίοΕϊ╣Μϋ░ΙίQΝόδ┤ϊ╕ΞόαψόΝθό┤ΜϋΘςώΘΞήΑΒόΜ┐ϊ╕φίδ╜ίχηόΔΖίΒγίνΨόζξόΑζόΔ│ύγΕό│ρϋΕγΎ╝ΝϋΑΝόαψίΛςίΛδϊ╕║ίδ╜ίχ╢ίξιίχγίφοόεψϊ╕ΛϋΘςύτΜύγΕίθ║╝ΜΑίQΝύΦρί╜Υϊ╕ΜΜ╣ΒϋκΝύγΕϋψζόζξϋψ┤ίQΝόηΕ╜{Σϊ╕φίδ╜ύγΕίφοόεψϋψζϋψφήΑΓίΗβίΙ░ϋ┐βώΘΝΎ╝ΝόΙΣίΠΙόΔΝβΥvόψΧϊ╕γϊ║Οό╕ΖίΞΟύγΕίΡ┤όΨΘϋΩ╒dΖΙύΦθΎ╝Ν1928≥q┤ϋΟ╖ί╛ΩίΥξϊ╝οόψΦϊ║γίνπίφοίΞγίμτίφοϊ╜ΞΎ╝ΝΜ╞κί╣┤ίΙζίδηίδ╜ίΡΟίΠΩϋΒαϊ║ΟύΘΧϊ║υίνπίφοήΑΓύΘΧϊ║υίνπίφοόαψόΧβϊ╝γίφοόικίQΝύν╛ϊ╝γίφο╛p└LΚΑύΦρόΧβόζΡίΖρϊ╕║ίνΨόΨΘΎ╝ΝϋΑΒί╕Ιϊ╕ΑϋΙυϊ╣θύΦρϋΜ▒όΨΘϋχ▓όΟΙήΑΓίΡ┤όΨΘϋΩ╗ώβνϊ║ΗύΦρό▒Κϋψφϋχ▓ϋψΣ╓νΨίQΝϋ┐αϊ╕°βΘςί╖▐pχ▓όΟΙύγΕήΑΛϋξ┐ΜzΜύν╛ϊ╝γόΑζόΔ│ίΠΝ╙ΑΜήΑΛίχ╢όΩΠύν╛ϊ╝γίφοήΑΜήΑΛϊζh╛c╒dφοήΑΜϊ╕ΚώΩρϋψ╛╛~ΨίΗβϊ║Ηϊ╕φόΨΘόΧβόζΡήΑΓϋΑΝίΡ┤όΨΘϋΩ╗ίQΝϊ╣θόφμόαψϊ╗ξέΑεύν╛ϊ╝γίφοϊ╕φίδ╜ίΝΨέΑζύγΕίξιίθ║ϋΑΖίΤΝίΖΙϋκΝϋΑΖϋΊnϊ╗╜ό░╕αqεύΧβίερϊ║Ηϊ╕φίδ╜ίφοόεψίΠ▓ϊ╕ΛήΑ?/span>